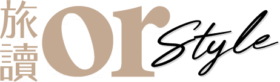【作者】 鄺介文 文_ 鄺介文/ 旅讀 繪_王盈穎/ 旅讀
2021年7月號 第113期
2021-07-12
疫情罩頂,戲院緊閉,各家片商無不面臨損益難關,紛紛推遲檔期。戲劇作為文學一類,不同於詩歌、散文、小說, 作的時候自由,讀的時候自由,須得通過商場機制檢驗,始能存活於當下,枉論見聞於後世。而竇娥故事所以能夠搬演再搬演、改編再改編,就是大字不識幾個的升斗小民,也知道六月飛霜、順水推船的典故,不可不謂滲透人心。
是家庭通俗劇 也是社會公案劇
竇娥之冤,冤在忠孝節義一應俱全,卻在現世不安穩的前提底下,落得個歲月不靜好。因為四十兩銀子的債務,小小端雲賣作蔡家童養媳,改名竇娥。也曾舉案齊眉,而後丈夫病死;也曾婆慈媳孝,可惜好景不常。因為婆婆幾個閒錢,終究引狼入室,觸發連串危機。尤有甚者,公權力無從發揮作用,竇娥心願只能一退再退,退到冀望來生真相得以大白。
余秋雨試析雜劇兩大精神主調,一是傾訴整體性的鬱悶和憤怒,二是謳歌非正統的美好與追求。關的作品多半屬於前者。
一如當今影壇,法庭題材為數眾多,幾獨立成一個類型,元曲之中,公案同樣受到歡迎。畢竟當朝尚武輕文,諸多官吏可能甚至胸無點墨,導致弊端叢生。通過戲劇,百姓得以投射自我,進而一吐怨氣,此即悲劇洗滌人心效果。
笑著笑著就哭了 哭著哭著就笑了
竇娥是否感天動地似無疑問,然而,竇娥是否「本格悲劇」卻曾經引發討論。
緣起王國維於《宋元戲曲史》中如此寫道: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構其間,而其赴湯蹈火者,仍出於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往後錢鍾書卻反駁道:中國戲曲家在悲劇創作上是失敗者。
固然,雜劇礙於演出模式(戲曲是門綜合性的藝術,戲曲劇場也是個綜合性的場域,來到這裡不單單要聽戲,還要與朋友聯繫感情,因而邊看邊聊邊吃邊喝不但是家常便飯,更是理所當然),難如歐美劇場個個都正襟危坐、全神貫注,勢必安排若干插科打諢,始能吸引看客。比諸《竇娥冤》一劇,包括賽盧醫自介「死的醫不活,活的醫死了」、桃杌自曝「來告狀的,就是我衣食父母」,不過都是小小的滑稽橋段,並不影響整體悲劇含量。
竇娥不夠冤?重理悲劇定義
兩位學者展開長達半世紀的學術爭辯(儘管王國維早於一九二七年投湖自盡,這場對話只限單向討論),援引西方理論檢視中國戲曲,癥結有二:一、竇父高升歸來、重審冤案,楚州大旱三年的真相水落石出,削弱力道;二、竇娥際遇偏向造化弄人而非性格缺陷,使她缺乏內在掙扎,行為過於被動且單一。
眾所周知,中國喜好團圓結局,就是明代傳奇動輒四、五十齣(詳見P.122「一年讀罷」專欄),生旦二人千里乖隔、命途多舛,情節最終必成眷屬。而《竇娥冤》礙於雜劇四折體例,關漢卿偏偏將她指天罵地的高潮段落放在第三折,單只為了父女人鬼能夠重圓,造成第一、第二折場次擁擠、線頭繁多,結構大抵看來不甚勻稱。沒能在正反搏鬥、天人對峙最緊繃的時刻戛然而止,留待觀眾步出劇場以後自行回味尋思,確實是《竇娥冤》一大遺憾。
如果蔡婆不軟弱 竇娥不固執⋯⋯
其次,竇娥經歷確實大多屬於命運悲劇。即使在第一折開初,賽盧醫、張驢兒尚未登場,單單七歲賣作養媳、十八歲丈夫亡化,便足夠她自問自答「竇娥也,你這命好苦也呵」,枉論種種人善得人欺的遭遇,彷彿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用以試驗人性的脆弱與堅韌。然而,面對各種衝擊天外飛來,竇娥下場如此,恐怕並不全然只與命運相關。
單單第一折裡,蔡婆的優柔寡斷盡顯無遺,竇娥與之共處長達十三年,沒理由不摸透婆婆底細,丈夫亡故以後,自然成為一家之主。兼之從小寄人籬下,長年養成一清二白的性格也是無可厚非。面對張驢兒問道:「你要官休?要私休?」竇娥二話不說選擇前者,一來相信自己,二來相信真理。可以說其固執是深化她惹人憐惜的原因,其固執也是催化她迎向終局的原因。
忠孝難兩全 情義我心知
錢鍾書所以認為竇娥抉擇不構成性格悲劇,在於傳統中國思想當中,關於美德總有高下分別。比諸忠孝兩難的時候,多半選擇忠(可見紀君祥《趙氏孤兒》);情義兩難的時候,多半選擇義(可見白樸《梧桐雨》)。於是,一旦竇娥將貞節觀念置於一切之上,即使死亡迫近,也能夠毫不遲疑地從容赴義,因而缺乏像是馬克白夫婦那樣,陷於野心與仁愛之間難以自拔的糾結。
綜觀全劇,竇娥確實一條腸子通到底。無論面對婆婆再嫁、自己再嫁、惡霸要脅、昏官侵逼,心心念念全是「我將這婆侍養,我將這服孝守,我言詞須應口」,沒有半點猶豫( 詳見P.59引文),使得性格不如莎翁筆下角色複雜。
然而,我們也不妨質疑錢鍾書等五四文人,對於文學理論亦存在高下偏見:悲劇優於喜劇,性格悲劇優於命運悲劇,詩優於劇,西方批評優於中國批評──於是一味將竇娥之冤套入西方理論檢視,得出「中國戲曲無悲劇」的斷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