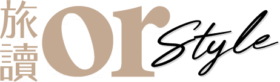文_黃彥綾/旅讀 圖_李智凱/旅讀
2025-04-18
在伊斯坦堡出差的短短幾日,我們就遇上兩次劇組拍攝。很恰巧地,一次是在貝伊奧盧一家雜貨舖撞見,另一次即是在巴拉特(Balat)。
身著筆挺軍裝的高大男子與手捧鮮花的少女,腳步輕盈地踩在石塊鋪排的街道上,空氣中流淌著戀愛的酸臭味。沒想到巴拉特街區那成排色彩艷麗的公寓,這麼適合當作「霸道軍閥愛上落魄千金」的背景板。
以紅磚構築的法納爾希臘正教學院是街區內最顯眼的地標。始建於1454 年,被譽為「伊斯坦堡的紅宮殿」,如今仍有少量希臘學生在此就讀。©李智凱/旅讀
色彩斑斕,文化斑斕
巴拉特為法蒂赫區下的一個街區,距老城市中心約莫半小時車程。巴拉特坐落於地勢陡峭的山坡上,彩色公寓錯落有致。然而,如今這片與老城區散發著截然不同氣氛的街區,卻曾是帝國興衰的縮影。
15世紀末,巴拉特成為猶太人的聚居地。1492年,西班牙君主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貝拉一世奪下安達魯西亞最後一座穆斯林城邦格拉納達,並頒布《阿爾罕布拉法令》,強制驅離猶太人與穆斯林。當時的蘇丹巴耶濟德二世以開放的態度,接納這波難民為公民。
猶太人的到來不僅為巴拉特帶來18座猶太教堂,更促進帝國的經濟發展:伊斯坦堡繁盛的印刷與絲綢業都可見其蹤跡。此外,由於巴拉特與希臘人為首的社區法納爾(Fener)相接,也有許多希臘人及亞美尼亞人定居此地,從而形塑一個多元的聚落。
位於該條街道上一個三角點的Cafe Naftalin K以溫馨復古的氛圍著稱。店內提供土耳其咖啡與手工甜點,是漫步巴拉特的歇息好去處。©李智凱/旅讀
帝國餘暉人口出走
然而,蘇丹喜怒無常,帝國乃至於日後的土耳其共和國面對如此複雜的組成人口,也並非始終保持著包容的態度。18世紀,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團體之間的對立日益嚴重,到了19、20世紀,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進一步分化了社區。尤其是20世紀初,希土戰爭及土耳其政府一系列的民族政策,使得希臘人與亞美尼亞人遭受驅逐與迫害;二戰後,大量的猶太人陸續移民至以色列,巴拉特與法納爾的族群結構進而產生變動。
隨著近代原先居民大量離開,這片曾經繁華的街區開始衰敗,並逐漸吸引來自安那托利亞內陸的穆斯林,轉變為一個以藍領階級為主的區域。由於長期缺乏投資,巴拉特在20世紀後期成為一個較貧窮的地區。千禧年以來,伴隨伊斯坦堡都市計劃的推動,這片曾經沒落的社區才進行大規模修復,不少藝術家與在地青年們重新進駐閒置的空間,開設咖啡廳與工作坊,為社區注入一股波西米亞式的不羈魅力。
Gen Antik Café 小小的空間內,充斥著店主的古董收藏。復古與華麗兼具,讓人得以一邊品味咖啡,一邊欣賞時光的痕跡。©李智凱/旅讀
漫遊找尋巴拉特新生
現今的巴拉特與法納爾,因街道上繽紛的宅邸成為伊斯坦堡的網紅打卡點。當訪客步入這片依山而建的社區時,從街道上方俯瞰,便能看到層層疊疊的連棟公寓。仔細一瞧,每棟房屋或是有著圓拱窗與石砌裝飾,或是帶著向外凸出的木製陽台(Cumba),融合鄂圖曼式與新古典風格。
踩著緩慢的步伐在街區彎彎繞繞──你也必須如此,坡道實在過於陡峭──偶爾回頭遠眺,便可見赭紅色、鵝黃色、暖橙色、寶藍色……各式鮮明的色彩,將後方的金角灣襯映著更加蔚藍;居民們晾曬的衣服依舊在樓棟之間搖擺,教堂的鐘聲依舊飄盪,街區好似重返其燦爛年代。
BalaRt Art House主要販售以巴拉特建築為造型的擺飾與磁鐵,每一具皆為職人親手製作彩繪,是我本次漫遊巴拉特最滿意的愛店!©李智凱/旅讀
****************************************
更多內容請詳旅讀《在伊斯坦堡尋找鄂圖曼》
2025年4月號 第158期
https://orstyle.net/product/no158/
****************************************
黃彥綾
《旅讀》雜誌企畫編輯。1995年出生,中壢高中、新竹教育大學畢業,主修心理諮商系,卻因離不開文字,在校輔修中文系及文化與藝術產經學程。貓派,海派,期望未來都能以文字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