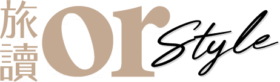【作者】 文/鄭有利、黃麗如 圖/聯經出版 提供
2021-01-26
南極,是旅人的夢土。
曾經去過南極的人,都有一段被凍結的時間,那段時光所發生的故事,已被壓縮、真空在剔透的冰層裡,泛著藍藍的光,閃爍著魔幻時刻。
過去的探險家,以插下旗子作為自己探險生涯的里程碑;現在的旅人,則在已知的地理疆界,從事不同的追尋。不管是體力上的挑戰還是形式上的超越,雖然沒有地理大發現,但自我的探索源源不絕、驅使探險魂往地球最南逼近。
《呼吸南極:在世界盡頭找一條路》作者鄭有利、黃麗如去過南極多次,記錄了一篇又一篇最初誘發他們前往南極的知名探險家的故事,並且寫下追尋這些旅人們足跡的歷程。除了書寫歷次行程最深度的觀察、拍攝最精采的圖片,還為準備去南極旅行的旅人提供了最實用的資訊,方便大家閱讀、帶著走。了解南極,不能不看本書;前往南極,更不能沒有這本書。
《呼吸南極》由聯經出版推出,底下為本書第一章精彩節錄:
寂靜大地裡的冰聲響
冰,可以堅硬得讓行走在南極的船隻擔憂;也可以柔軟得融在威士忌裡,增添酒質的甘美。冰,看起來冷酷安靜,但當他發出聲響時,就像一顆子彈竄出,巨響之後,總是有些東西徹底的改變。2010年3月抵達南極半島的尼可灣(Neko Bay)時,是仙境般空靈的好天氣,這個港灣純淨得發亮,如果人間真有仙境,大概就是這個模樣。
在準備走進仙境裡的時候,探險隊長Brandon說:「盡量不要走在沙灘上、往山坡上走,看起來永恆的風景,其實變化快速。」我當時不懂他的意思,因為眼前的風光、就是一張晾在藍天白雲下的明信片、是不會有任何風險的美麗。越往上爬心臟跳得越快,每一個踏步就多看到一分港灣的角度、那種漂亮是美到讓人頭皮發麻、讓人亢奮的激動。
爬到至高點、躺臥在白得純淨、藍得深邃的港灣前,眼前的冰河是遼闊的白色沙漠,風,揚起遠方的冰沙。同行的友人Diana被景象迷得發癡地說:「登岸的時候,我連拿相機都懶,因為眼前的風景是相機裝不進去的,我只想坐下來睜大眼睛看。」我們呆望著這個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見到的景致。突然,轟隆一聲有如煙火爆開的聲音傳來,眼前的冰河前緣剝落一塊,墜入到海中的衝擊力道掀起一陣巨浪,浪拍打在沙灘上,企鵝們紛紛被捲入海裡。
剎那間,我才明瞭Brandon所提醒的不要離海邊太近。冰河巨響帶來的漣漪持續了十五分鐘才慢慢的平息,海灣又重回平靜,一切就像什麼都沒發生過。探險隊的成員有感而發的說:「好好珍惜眼前的冰河景色,南極有250條冰河、有八成在消退,若南極的冰全部融化,海平面會上升75公尺。」我無法想像海平面上升75公尺是什麼樣的世界,但在那一刻,我只想好好的靜坐在大冰河前、呼吸著冰涼的空氣、任憑強烈的紫外線侵蝕皮膚,就算曬傷或受凍都甘願。當我被上升75公尺的海洋吞噬時,我會記得眼前的冰風景。
任性且狂妄的風
風和日麗的南極風景有如天堂,就如同半島上知名景點「天堂灣」(Paradise Harbor)的名字。但多半的時候,南極的氣候就像探險家的筆記一樣,充滿了變數,有超級的風暴、不按牌理出牌的海流,他就是因為不羈,才讓人神往。南極,又被稱為風極,造訪過南極的旅人,更能體會「風」「景」這個詞彙的意義。
對這種依賴海上航行的旅程,風向、風速決定了旅程的一切,謝克頓的堅忍號之旅,因為風向耽誤了數月的行程。在我們的南極之旅期間,有時候陽光燦爛,但海面上白浪滔滔,探險船根本無法靠近港灣、下錨,橡皮艇也無法在巨浪中乘風破浪抵達登岸點,旅人只能站在甲板上、望著岸邊的十幾萬隻企鵝興嘆,懊惱著昨天入睡前只跟老天爺祈求給我一個藍天白雲的好天氣,忘了強調要風和日麗。
南極的風,很狂,狂妄到有壓倒性的危險。地質學家普利斯特雷在《南極冒險》寫道:「每次風一稍停,我就朝風摔倒;而每次大風吹來,我又被風穿彎,有十幾次,我被風颳得站不住腳,撲向地面,甚至撞到堅硬的石頭。」我曾經覺得他的描寫太誇張,但當自己實際經歷過,才明白被風打趴在地面的痛。
2 0 1 0 年的南極夏末, 我們的船很驚險的在米肯森港(Mikkenson Harbor)登岸,為了看企鵝群必須翻過一個小小的山頭。通常這種小土丘約十分鐘的腳程就可以走到另一端,但那天早上風大得可以把人壓倒,踩在雪地裡、一步一腳印的往上爬、還要承受風的壓力,小土丘的旅程變成跋山越嶺的難度,有的同伴索性蹲下或撲倒,想等強風過了再繼續行動。
但風像是發了狂般永無止盡的吹,毫無終點、也沒有疲憊的姿態,它的力道打得我舉步維艱。那次登岸,我幾乎都是以背部迎風或是躲在友人身旁,希望更多的阻力讓我不至於跌落山谷。然而最後還是被風撲倒,只能趴著一步一步匍匐前進、謙卑的接受大自然的力量。
到不了的南極
多年來, 我以為我已見識到南極各式各樣的「冰」、「風」、「景」,但這塊神奇大陸,總是有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會發生。南極的旅程充滿驚奇與不可控制,就算我們在探險設備精良的時代,也無法控制翻上來的浪、恣意竄流的浮冰。南極的各種風景我都甘願接受,只是我從沒想過,一趟南冰洋的航行也是有可能無法登岸、到不了南極大陸。2010年在南極的船上,遇見英國夫婦黛安娜和史都華,當船剛離開烏蘇懷亞碼頭時,他們兩人興奮得大叫大跳,黛安娜說:「這是我們第三次參加這個行程,卻是第一次如此順利的出航。」
他們連續三年從倫敦飛到阿根廷再奔赴世界盡頭的港口烏蘇懷亞、前進南極,2007年遭逢Explore II事件、船班大亂,他們被搞到沒有機會登船;次年,他們再次造訪南極,黛安娜說:「那一回更妙,船只走了一天就因為天氣太糟而折返,所以是德瑞克海峽一日遊,我們只好無奈的飛回倫敦。」2010年3月,他們終於如願以償登上南極大陸,行程快結束的告別派對上,黛安娜開心得猛灌酒、開懷跳舞,甚至把歷史學家衣服扯掉。她的南極夢走得太辛苦,需要大醉一場才夠。
我以為黛安娜的遭遇是特例,畢竟這十年來,天氣再怎麼不好,我都有抵達南極大陸,只是有時候風景陰鬱得讓人不想掏出相機。但2018年10月的南極之旅,在造訪南喬治亞和福克蘭群島後,我們的船遇到了超級風暴,浪很大、風很狂,我們緩慢的頂著風往南極靠近,當船駛達西瓦海灣(Cierva Cove)時,探險隊長廣播:「前面50公尺的那片大陸就是南極了!」我興奮得在甲板上觀看,雖然天色不佳、雲很低,但灰灰白白的蒼茫感對我仍有吸引力。每年年底踏上南極大陸,幾乎就是我這十年來固定的儀式,彷彿一整年紛飛的思緒都可以在這塊寂靜大陸上沉澱。
正當我準備回房間穿雨褲、披防寒衣、下船登上南極土地時,探險隊長廣播:「由於風浪實在太大了,我們無法搭橡皮艇登岸,之後幾天風暴會越來越大,為了安全,我們現在就要回航。」酒保端來了香檳,要慶祝我們「抵達」南極。這是我第一次拒絕喝酒,在經緯度上我們是抵達南極,但並沒有登上南極、踩踏南極大陸。
在甲板上望著南極大陸,他是那麼近,可是又不可親,我多麼渴望可以在冰上摔倒,痛快的感受從南極大地地心竄上來的冰與痛。當船往回開的時候,不禁感傷下一回抵達南極大陸不知何年何月?同行的旅人陷入集體沮喪,畢竟來一趟南極,時間和金錢都不是容易的事,有多少人有「下一次」的機會再從事一次南極之旅。
頓時明白,十年前黛安娜和史都華為何每天都帶著慶祝的心情悠遊南極,因為過去兩次旅行的失敗,讓他們珍惜每一天,能登上南極大陸真的是得來不易。但也是2018年登陸的失敗,我終於明白過去庫克、謝克頓必須回頭的心情,尤其謝克頓已經抵達南緯88度,就快到達南極點了,但天候就是不允許他再往南行。不管是數百年前或是此刻,南極依然是一切看天意的旅程,他的百變風景,只有企鵝可以概括承受。人類,在白色南國面前,只能臣服於他,在這裡發生的喜怒哀樂、登岸或不能登岸,全都是南極的風景。
就算企鵝已經是「適合」生存在南極的物種,經歷過冬之旅的薛瑞在見識過帝王企鵝艱苦的棲地後,寫著:「大自然是不肯通融的保母。」這句話,一直在我的歷次南極旅程中迴盪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