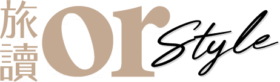【作者】 鄺介文 文_ 鄺介文/ 旅讀 繪_王盈穎/ 旅讀
2021年7月號 第113期
2021-07-19
自然,在此以前(尤其宋代話本)不乏關注平民角色的作品,卻從來沒有哪位文人如他一般,如此大量、如此刻意、如此悉心地對於底層全盤描寫。如果竇娥寫的是可遠觀而不可褻玩,那麼趙盼兒寫的則是出淤泥而不妖不染。
誰說妓女不能是俠女?
劇本全名「趙盼兒風月救風塵」,指的是施展風月手段,拯救風塵中人。妓女引章偶遇富少周舍,以為此生有望脫離秦樓楚館,不顧姐妹、老母、初戀好言相勸,自汴京遠嫁鄭州。一來是,周舍惡霸行事本性難移;二來是,賤斥娼優觀念根深蒂固,婚後落得家暴下場。趙盼兒與宋引章惟有姐姐妹妹站起來,青樓女子團結力量大,她們決計以智取勝,扳回尊嚴。
在此劇本當中,趙盼兒儼然不單是一血肉之軀,甚至成為關漢卿筆下的符碼,象徵身處下賤卻胸懷四方的族群(七匠八娼尚且如此,何況九儒十丐;漢人尚且如此,何況南人)。一如概論所述,元代演劇所以發達,既是作者苦無出口,也是觀眾苦無出口。可以想見,此時此刻,關漢卿與趙盼兒畫上等號,作者透過書寫角色一吐怨氣,觀眾亦透過觀看角色一吐怨氣。
一朝誤墮酒肉場 一世難轉風水輪
起初,作為歌者的宋引章已墮風塵,試圖經由婚姻反轉人生,然而何嘗容易?趙盼兒早替她唱出來了:待妝個老實,學三從四德;爭奈是匪妓,都三心二意。
當時對於妓戶的輕視,不是一朝一夕得以消解。只見引章如此念道「做一個張郎家婦,李郎家妻,立個婦名,我做鬼也風流的」,前頭洗白命運的天真,對比後頭事與願違的悽切,元朝社經地位之結構井然,可見一斑。
這時,宋引章其實有兩個選擇:窮儒生秀實與富二代周舍。浸淫酒肉場上日久,引章不免沾染拜金氣息,兼之「儒人顛倒不如人」的時代,讀書顯然是最無出路的職業。因而宋引章的抉擇,觀眾亦深能體諒。於是她就是偏執、就是駑鈍、就是不識好歹,口出「我嫁了安秀才呵,一對兒好打蓮花落」一類妄言,仍舊惹人憐惜。畢竟她人已在風塵,卻再墮風塵。
人在風塵,再墮風塵
第一張風塵網是先天的職業,第二張風塵網則是後天的婚姻。
原先拆白道字,頂真續麻,無般不曉,無般不會的引章,離了青樓以後,這才發覺自己一點生活技能也沒有。要做一個張家郎婦、李家郎妻,顯然是不合格的。於是周舍打罵不絕,甚至在趙盼兒找上門來的時候,撂下一句「丈夫打殺老婆,不該償命」「來則有打死的,無有買休賣休」,則婦女地位昭然若揭。
學者廖奔與劉彥君有一段文字,形容關的戲劇組織──一方面能從人物的現實處境出發,展開衝突,將矛盾一步步引向高潮;一方面又安排轉折移步換形,變化多端,使人無法預測情節的發展。──不但專指所有劇作的整體結構,光是《救風塵》一齣,用以形容宋引章與趙盼兒的角色功能同樣成立。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成日流連煙花的周舍,懂得甜言蜜語騙來感情;終年任職青樓的盼兒,又怎麼可能不懂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呢?自承娼家女「慣性發誓」,係趙以風月手段拯救宋於風塵之中的又一例證。後設看來,也等於是關漢卿本身對於天命的嘲弄。花花公子如周舍,一生說盡多少謊言,卻怎麼一旦對著明香寶燭、一旦指著皇天后土,那些謊言隨即具備效力了呢?
尤其元代社會體制使然,當朝作品不約而同出現虛無和宿命的傾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因果輪迴的成份或多或少都在雜劇裡頭出現。人的力量被削弱,天命被弘揚到了一個極高的位置,幸與不幸都來自於神,這是莫可奈何的時代印記。趙盼兒一席話不但反制周舍,同時叩問上蒼:假如真有善惡果報,哪來這麼多的生靈塗炭?──可以想見,當時演出,廣大觀眾聽聞趙的呼喊,思及自身,不免眼熱心酸。
可愛又迷人的正派角色
表面上《救風塵》不如關的其餘作品,比諸《 緋衣夢》或《蝴蝶夢》一般,怒髮衝冠、壯懷激烈。
就是對於政經與體制、個體與命運、空間與時代的投訴,亦隱隱約約, 縮至最小,整個劇本彷彿只是一張浮世繪。卻正因為相隔一層,如同盼兒之於引章的旁觀者清,你我之於盼兒同樣旁觀者清,她的風月手段、風塵處境才更使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關漢卿以輕巧的節奏、靈動的語言調度了一個無懈可擊的故事。《竇娥冤》所以雋永,在於命運使然;《救風塵》所以耐讀,卻是性格使然。學者徐子方說:「在她身上既無值得諷刺和嘲弄之處,又無『恰當中的不恰當』從而招惹幽默微笑之處。」興許正是如此,趙盼兒不畏女性/妓戶雙重弱勢,自信挑戰男性/富家雙重優勢,使得歷來萬千觀者與讀者,能夠從中賦予寄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