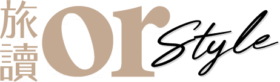【作者】 鄺介文 文_ 鄺介文/旅讀 插畫_楊喬勻/旅讀 圖_視覺中國
2022年6月號 第124期
2022-06-14
政客不外如此,生前追逐權勢財貨,死後還得追逐歷史定位。尤其更迭頻仍、時局紊亂的兩晉六朝,之所以無法出現漢唐那樣的承平治世,不少史家以「清談誤國」四字蓋棺論定,罪魁禍首多半指向王衍等人。甚至王衍一生心高氣傲,臨終之際亦不免自省: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這不只是歷史定位,還是自我定位了!
東漢就有政論節目
其實,清談也並非一開始就是「浮虛」的,它是被動與主動種種因素交相作用而成的風尚,前身可以追溯至東漢太學。
太學是古代官辦最高學府,在不同時代有不同名稱。五帝稱為成均(即今日韓國成均館大學命名由來)、夏朝稱為東序、商朝稱為右學、周朝稱為上庠,不一而足。其設置目的,據董仲舒的話是「以養天下之士」。這些通過考核的儒生集結於此,修習儒學五經及其周邊傳注,以便將來步入政壇,謀得一官半職。
東漢後期,外戚攝政、宦官專權、農民起義,熟讀論孟的儒生們,自許有揚清激濁的責任,於是群起進諫、發表彈劾,批評那些目無法紀的禍源。他們將當時臧否人物的矛頭,從士族名流轉向了亂臣賊子,試圖避免國家走向覆滅,此即「清議」。換句話說,這是一檔由太學儒生主持的政論節目。
禍從口出到多說無益
一如現今職場,同期同事、同學校友多會彼此提拔照應,那些已在政壇、未入政壇的太學學長弟們,也是相互拉抬幫襯。從武帝初期的五十人,到王莽篡漢的一萬人,逐漸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東漢末年的兩次黨錮之禍,正是宦官集團眼見清議集團可能威脅自身利益,繼而發起的「整頓」。而兩次黨錮之禍皆由清議集團吞下敗果,宦官持續坐大,使得東漢終究迎來黃巾之亂,中原大地陷入了長達三百餘年的兵馬倥傯的局面。
然而,敗果歸敗果、坐大歸坐大,黨錮以後,清議風氣並未消止。相反地,太學儒生情緒更形高張,似將論政一事視為己任,與宦官長期勢同水火。真正使得知識份子選擇噤聲的,是曹氏父子。司馬光《資治通鑑》有言: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曹操與曹丕,正是滅了「天下有道」最後一點火光的關鍵。
不給清議就清談
清議與清談,時常使人傻傻分不清楚。甚至魏晉當時文獻,也有二者混淆互涉的情形。事實上,清議可以是清談前身,卻不是清談本身。東漢的「清」議是清流議政;魏晉的「清」談是清虛談玄。前者是入世的、儒學的;後者是避世的、道家的。士大夫們從入世地、積極地兼善天下,轉而避世地、消極地獨善其身,很大一部份原因在於目睹孔融、楊修惹禍上身。
他倆皆與曹家交好,卻讓曹操欲加之罪地胡亂尋了幾個藉口處決。前者是「招合徒眾,欲圖不軌」,後者是「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世人眼見,曾經可與曹操一搭一唱的二人,最終還是一頭撞死在權力高牆之下,既然無力衝撞執政,索性率先自我審查。漢武帝罷黜百家以來,數百年嚴絲合縫的思想真空,就此破開一絲罅隙,照進了道家的無與佛家的空。
風流雅緻的腦筋急轉彎
狹義的清談,可以如此定義─就內容言,談的是三玄(周易、老子、莊子及其延伸);就目的言,為的是交流;就形式言,論而有丰采。
亦即,相較單人政見發表的清議,清談則是多人哲學沙龍。政見發表是一人說、眾人聽,仰賴講者魅力;哲學沙龍是一人主持、多人來回,主持魅力固然重要,水平與之不相上下的與會辯士同等重要。
既然講究魅力,則久而久之,難免文勝於質、丰采重於論證。一般而言,學者多視何晏、王弼為清談祖師。二人對於老莊頗有識見、能說能寫,史稱正始之音。然而及至王衍一代,相似的題目、同樣的集會,結果卻落得清談誤國,恐怕因為他「口中雌黃」的緣故。成語信口雌黃出自《晉書》,形容王衍辯論的時候,倘若邏輯不通,隨即更動說詞,藉由「魅力」敷衍過去,仍舊贏得眾人讚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