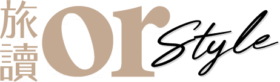【作者】
文_ 郝譽翔/ 旅讀、Doris/ 旅讀、黃彥綾/ 旅讀、黃莠苓/ 旅讀、部分文字摘錄自網路與書──郝譽翔《經典3.0夢幻之美──聊齋之美》 圖_ 圖蟲創意
2022年8月號 第126期
2022-08-02
我們讀聊齋,不只是在讀它那充滿了想像力的精采故事,更是在讀中國文化中美的精髓,並且要以此無限之美,點染我們自己有限的生命。──郝譽翔《經典3.0夢幻之美──聊齋之美》
藉奇詭,叩問蒼穹
中國文人自古以來就多有寫作筆記叢談的傳統,但是大多數都把它當成是閒暇之餘的消遣,以為新奇有趣,譬如同樣也是清朝的著名文人紀曉嵐,就有《閱微草堂筆記》一書,而大文豪袁枚也寫過《子不語》,記錄了許多奇聞軼事,以供眾人欣賞和流傳。
乍看之下,上述這些作品似乎和《聊齋》相當近似,故事來源不是作者從親友之間聽說而來,就是轉寫自中國傳統的志怪小說,然而《聊齋》又何以能夠從諸多的作品之中脫穎而出,成為經典代代流傳呢?就在蒲松齡寫作的態度大不相同,《聊齋》對他而言絕非消遣之作,而是富有深刻的寓意,更是一個亂世文人寄託懷抱的「孤憤之書」,而它的精神源頭,更可以往上追溯到屈原的〈離騷〉、〈九歌〉和〈天問〉。
屈原遭到楚懷王放逐,浪游在汨羅江畔,鬱鬱不得志,於是才有了〈離騷〉諸作,他下至黃泉,遨翔八荒九陔,叩問天神,探訪幽冥,卻四處尋覓知音卻不可得,至於〈九歌〉和〈天問〉,不也同樣都是詩人在朝向另外一個非現實世界的質疑和叩問?屈原以此來打破時空的限制,以無限,來求得自己有限之身的解脫。故蒲松齡談鬼搜神,也不只是設意好奇而已,更是一種精神上孤獨的終極美學,才有了集大成的《聊齋誌異》,也才能夠超越中國志怪小說中樸素的原始思維,而達到了人文的高度──自我的解放,甚至是被污濁人世所遮蔽了的「美」。
孤獨的終極美學
蒲松齡以《聊齋》為苦悶的現實人生,打開了一個充滿了超現實華麗想像的美的世界,也轉化了現實中必然存在的醜陋與惡,而這也是《聊齋》中的女鬼或狐狸,往往比人還要良善美麗的緣故了。所以蒲松齡喜歡寫美女或是麗人,還常以她們的名字作為篇名,譬如〈嬌娜〉、〈小謝〉、〈嬰寧〉、〈珊瑚〉、〈翩翩〉、〈菱角〉等都是,彷彿人影綽約,暗香浮動於紙端。
《聊齋》不僅人物美,動物美,景致美,就連語言也是精緻無比。蒲松齡刻意使用駢文寫作,譬如〈嬰寧〉一篇,寫王子服因為思念嬰寧,決定自己前往山中探訪佳人,一路走來只見:
亂山合沓,空翠爽肌,寂無人行,止有鳥道,遙望谷底,叢花亂樹中,隱隱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見舍宇無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門前皆柳絲,牆內桃杏尤繁,間以修竹,野鳥格磔其中。
寫山景以「亂山合沓」,寫空氣以「翠爽肌」,文字如此簡潔,嬰寧的住處又是如此「修雅」,儼然形成一個絕美的詩的世界。所以若用恐怖鬼話的角度去讀《聊齋》,必定會大失所望的,但若說蒲松齡把鬼狐寫得像人一樣親切,那倒也未必,這些鬼狐所散發出來的絕美,又哪裡是庸俗的人類可以相比的呢?
所以《聊齋》帶給當代讀者最大的啟示,無非書中所呈現出來美學世界,正是延續了晚明從《牡丹亭》、《桃花扇》乃至於《陶庵夢憶》等傑作,而集中國文化燦爛顛峰之大成。這些作品無一不是由「美」入「情」,然後由「情」見到了人心的可貴,卻也同時見證了人類的渺小、無奈、悲哀和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