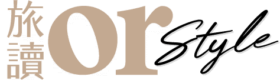文_鄺介文 圖_圖蟲創意、旅讀、Cheerimages
2025-01-15
作文說穿了無非談情,擅作文學者無非擅談感情者,無論親情、愛情或人情。太白一生寫詩無數,所有酒後吐的真言,其實是他對於感情的箴言。
如前文所述,倘若李白係以友情的視野來看待親情與愛情,那麼他的那些羅曼蒂克主題情詩寫的是誰?答案是李隆基與楊玉環。放眼中國文學史,李楊戀情幾乎能夠獨立而出一套系譜,自李翰祥《楊貴妃》一路上溯,而有洪昇《長生殿》、白樸《梧桐雨》、陳鴻〈長恨歌傳〉、白居易〈長恨歌〉,體裁橫跨電影、南戲、雜劇、傳奇、古詩,如此洋洋灑灑不一而足,卻別忘了「始作俑者」,其實是李白的七言樂府〈清平調〉。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清平調三首〉

西安華清池 ©麥翔雲/旅讀
記者李白,長安後宮現場報導
長此以往,白氏版本〈長恨歌〉深植人心,幾成二人悲劇代名詞。而李白詩歌無數,偏偏挑出〈清平調〉作為情詩代表,有其特殊意義,據學者歐麗娟言:「這是天時、地利、人和俱足的一次奇蹟!」天時,指的是天寶初期欣欣向榮,社會氛圍由清雅轉為旖旎,宜於浪漫滋長;地利,指的是李白時任翰林供奉,得以長驅直入深宮內苑,近距離觀察描繪;人和,指的是唐玄宗的惜才與李太白的剖心,君臣之間有一定程度的相知。如此三者,造就往後所有李楊戀情文學皆無法企及的一項關鍵──
只有李白親眼目睹,只有李白親耳聽聞,只有〈清平調〉是紀錄片般的現場實況轉播,兼具時間與空間價值。無論白居易筆下的「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多麼纏綿緋惻,終究是後見之明,少了第一手資料的艷異豐潤。
史上最高級業配文
年過不惑,李白終於迎來人生轉機:獲玉真公主薦舉奉詔入宮。所謂翰林供奉,代換今日言語可謂「御用藝人」。玄宗本身酷愛藝文,一網打盡天下所有以書畫著名者、以樂舞著名者、以雜技著名者,當然還有以寫作著名者,通通納入長安隨時待命。比如〈清平調〉一詩的創作契機,正是某日李楊賞芍藥於興慶池畔沉香亭,一時興起,命樂師李龜年製作新曲助樂。不單旋律得新,唱詞也得新,於是下令「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隨即招來李白即席創作。
由此看來,後世曾有〈清平調〉是諷刺詩(以趙飛燕比擬楊玉環,暗指後者荒淫無度)的論調,完全空穴來風,係從安史之亂的後果,回推禍水紅顏的前因,卻忽略了李白創作當下/當時/當地的情境與心境。實則,〈清平調〉應當是一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業配文」──甲方出錢、乙方出力,不但配得賓主盡歡,尚且配出一種高級感、配得毫無銅臭味。

©陳鳳靈/Cheerimages
三詩一體,天上人間
既然是三首組詩,必須彼此參差錯落讀之,始能見其高妙。
三首的上半皆以花喻人、下半皆以人喻人。以花喻人、以人喻人在寫作上並非空前,甚至可謂俗套,然而李白精巧在於結構布局。我們不妨將三首詩的上半合而觀之、三首詩的下半合而觀之,會得到一個相對澄明的印象:
第一首上半是貴妃像牡丹、第二首上半是牡丹像貴妃、第三首上半是牡丹貴妃分庭抗禮,果然「長得君王帶笑看」;第一首下半是貴妃堪比西王母、第二首下半是貴妃堪比巫山神女以及趙飛燕、第三首下半是正面直書貴妃,她的儀態姿容足以消解無限悲恨。如此一來,讀者諸君應當能夠發覺其中奧妙,三首詩歌層層遞進,是從遠古到當下的一次過度,是從神話(天上女神西王母)到奇幻(半人半神巫山神女)到歷史(人間女神趙飛燕)再到現實(現代女神楊玉環)的一次過度。無怪乎玄宗聽了喜不自勝,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

©任中豪/旅讀
皇帝貴妃放閃光,閃開一株解語花
翰林院畢竟不是一般文武官員,只能聽命於廟堂之上,而是得以深入殿陛之間,親炙天子龍顏貴妃朱顏,乃至二人親暱互動、眼波流轉,俱在詩人心上筆下。關於李楊戀情,杜甫以降取材的文人不少,惆悵有之、感慨有之,個個寫出一幅世紀末的華麗,獨獨李白版本國色天香又活色生香,豐腴潤澤而不流俗,當之無愧是「史上最高級業配文」,箇中關鍵正在於此。
然而業配能夠使人信服,終究產品必須好用耐用。一如這般天時地利人和促成的奇蹟,還需一項前提:李隆基與楊玉環的真情。
且看文學史上相關題材,從〈長恨歌〉到《長生殿》,共通之處在於李楊之間是愛情無疑,並非尋常帝妃關係。即便後續輿論不乏禍水誤國的角度,卻鮮少有人質疑他倆只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楊貴妃除了光彩照人,陳鴻說她「善巧便佞,先意希旨」,《舊唐書》說她「智算過人,動移上意」,可以見得已然達到知己的程度,不僅止於以色事人而已。如今我們時常使用一詞彙「解語花」,正是唐明皇用以形容楊貴妃的。

©圖蟲創意
迎來愛情的春天
上述種種機緣揉合出了〈清平調〉這次奇蹟,李白本人真淳的性格同樣助了一臂之力。卻別忘了,寫作當時他已四十三歲,相較同齡文人多半有顆老靈魂(陳子昂不過卅六歲便開始念天地之悠悠),李白筆下的「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讀來幾近有種回春之感──陷入愛情的李楊回了春,旁觀愛情的李白回了春,連帶使得眼下閱讀愛情的你我也回了春。李白畢竟是永遠年輕的彼得潘啊!
我們總是先在文學讀到愛情,才在人生體驗愛情,而每個人的戀愛史,可能都是從「妾髮初覆額」開始的。直到日後回憶起來,方才驚覺那樣「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的過往,原來是愛。乃至千里之外/千年以後,我們撥開歷史因果重重迷霧,不去先入為主,不去事後諸葛,設身處地地靜心重讀〈清平調〉,興許得以收獲李白創作初衷,原來不是諷刺,原來不是挖苦,原來是愛。
****************************************
更多內容請詳旅讀《歡迎加入太白粉!》
2025年1月號 第155期
https://orstyle.net/product/no15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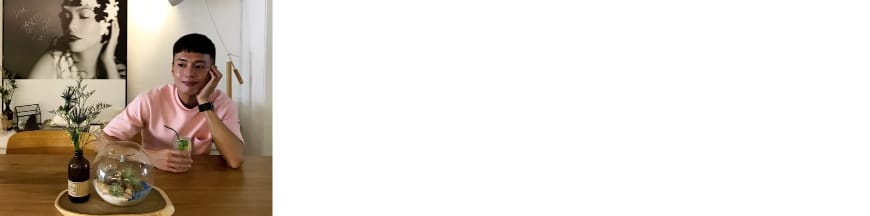
鄺介文
現任旅讀雜誌執行總編輯。師大附中、政大中文系、臺大戲研所畢業,主修戲劇理論、戲曲編劇及表演。香港出生的臺北市民。曾獲臺北新北臺中宜蘭教育部香港青年等十數文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