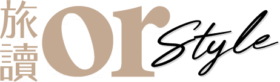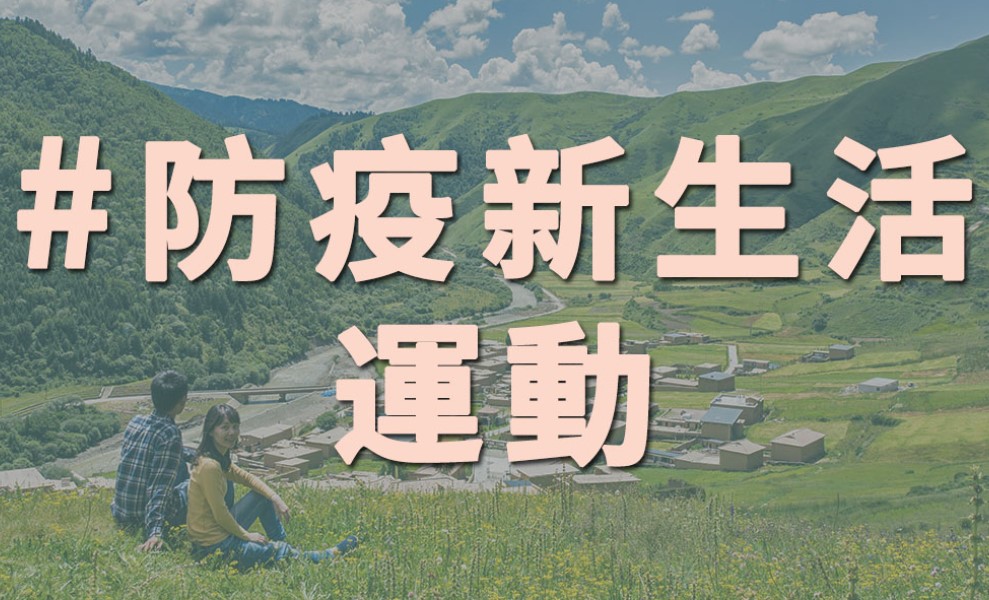文_ 甘炤文/ 旅讀中國、繪_ 黃鈺真/ 旅讀中國、圖_ 麥翔雲/ 旅讀中國、CTPphoto、視覺中國
特別感謝_ 發現者旅行社、李茂榮先生
2025-04-28
阿里三圍,昔我往矣:攀越世界屋脊的屋脊
來到極境中的極境,毫無疑問,眼下擁有全世界最壯麗的天穹、最純潔的湖泊和雪峰、最虔誠的信仰、最靈動活潑的生機,以及最古老也最深情的大地……邁步的雙腳或許疲憊,無邊的風景卻足以滌淨旅世者惹身的塵埃。沿著五色天路漫行,在世界屋脊的屋脊上展開一場壯遊,每個人終其身總要有一次的:西藏.阿里.大北線。
一千多年前,詩仙李白登臨川地,有感於道途艱險,遂留下了驚愕的絕唱:「噫吁!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也不怪李白如此小題大作,在那個往來運輸只仰仗車馬與舟船的年代,由關中至西南地方的交通已屬煩難,何況盛唐武功縱若蓋世,鞭長總未及與巴蜀相毗鄰的青藏高原──那是另一塊古老的土地,地勢更高拔、位置更迢遠、族群更特異,且由足以和中原王朝分庭抗禮的吐番政權所把持;就是天上謫仙,在當時也無緣親炙這塊如今公認為全世界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西藏,歷史上或稱西羌、吐番、烏思藏、土伯特……無論採行何種說法,大抵都囊括了青藏高原的本體。儘管隨著科技與交通的發展,西藏不再神秘蒼茫如昔,但那份始終遺世獨立的靜定姿態,使得它仍舊成為許多旅人魂牽夢縈的:永遠的他方。
宛如曼陀羅般的天路之旅
西藏旅遊中最經典也最刻苦的「大北線」,就坐落在這片廣袤難蹤的雪域上。以拉薩為原/圓點,往西南經日喀則的江孜、薩嘎,阿里的普蘭等地,至札達、日土一帶後再沿順時鐘方向折返,穿涉一部分的藏北無人區(包含那曲),復回到聖城拉薩。全程逾五千公里,高點則在海拔五千公尺以上,完整的大北線路程就像是佛家理想的宇宙模型「曼陀羅」,自成一圓滿的週期。
除卻並稱「阿里三圍」的普蘭(雪山圍繞之地)、札達(土林圍繞之地)和日土(湖泊圍繞之地),大北線上同樣收攝了許多自然與人文的精華景致,比如被許多探險家視為終極挑戰的喜瑪拉雅山和希夏邦馬峰,比如夕日間傾覆殆盡、詭秘消失的古格王朝,比如身披一襲「軟黃金」的藏羚羊、神出鬼沒的瀕危物種雪豹,更甭提岡仁波齊、瑪旁雍措等跨宗教的神山聖湖群了。
而作為大北線上最受矚目的旅遊地域,過去阿里人曾戲稱:「這裡又高又遠又荒涼,也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要想走闖天路、攀越世界屋脊的屋脊,除非骨血裡烙印著如同藏民般耐勞不畏高寒的基因,能夠忍受長時徒步的艱苦,否則對一般旅人而言,「駕車」依舊是目前完成整趟大北線旅程唯一可行的方式;也因為如此,夏、秋等觀光旺季期間,慣常可見越野車組成的車隊呼嘯過大地,在這條經典的旅遊環帶上留下撩亂的轍痕。
據聞在上個世紀六七○年代,駕車師傅一度成為藏家挑揀「女婿」時的熱門人選──理由無他,要想在洪荒草昧間走闖、為偏遠地區捎來物資,有什麼要比司機更現成的職業?當地甚至將此類現象編派成歌謠傳唱一時:「方向盤往右轉,給爸爸帶來了菸葉;方向盤往左轉,給媽媽帶來了頭巾。」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清晨,金黃色的朝暾映照於冰煙迴環的雪山之巔,跌宕起伏的峰巒紛紛髹上一抹異彩,沿著地平線開展各自的姿態。埡口地帶,五色經幡正隨過境的大風揚向天際,更遠的地方,幻變的浮雲時而沖散出裂口,任由陽光傾瀉;時而又聚攏成渦團,在曠野處投下巨大的陰影。愈發濃鬱的雲層終於逼出銀針般的雨線,絲絲縷縷洗去天地間的塵氣,裸出轉經路上一摞摞質樸而光潔的瑪尼石堆……這些,無疑都是大北線上的日常即景。除了偶現的牧民形跡,藏羚羊、野驢、旱獺和其他生靈才是大地的主角,牠們以先祖曾經活躍過的姿態持續在這片遼敻的草場間孳衍,將人煙罕至的蠻荒轉化為野性十足的樂土。
緣著大北線展開旅程,參與者每每要驚豔於週遭瞬息萬變的景觀──好像無意打翻了女媧的煉石缸、拗斷了江淹的五彩筆,所有感官都沉浸於斑斕的風光色相間,神識不免因此感到有些暈脹、陶然──那樣奇崛深秀的美,原也應以相應的勞頓為代價,好比旅人得先忍受簡陋的食宿環境、顛簸無盡的車行,而惱人的高原反應亦有可能一路相伴,成為肉身登峰造極之際的修煉。
早在一九二四年,知名的探險家亞歷珊卓. 大衛. 尼爾(Alexandra David-Néel) 就曾設法穿越嚴密的防線,成為首位成功進藏的歐洲女性。降及九十八歲生日大壽,她猶仍對這樁盛年往事念念不忘,提筆獻上了自己的最高禮讚:「我應該死在羌塘,死在西藏的大湖畔或大草原上。」
是這樣一處絕美與荒涼、生機與寂意並行不悖的所在,歷久彌新的西藏、阿里和大北線,彷彿自前世起便守望著旅人今生歸來,翻越一座又一座雪山、穿涉一座復一座湖泊,直到覓得心中永恆的香巴拉。
內容摘自旅讀《西藏 阿里》2017年3月號 第61期